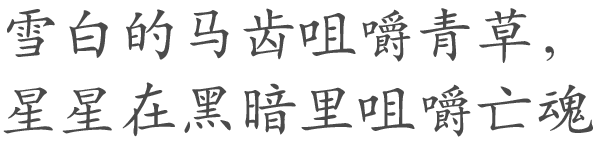专访埃莉诺乐队|“Focus”,中生代乐队的坚守与进击

埃莉诺乐队(ELENORE)成立于2009年,在成立的第十年,他们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全长专辑《光芒万丈》。 “shine a light, shine a light”,呼唤里包裹的某种抽象、向好的期待,也隐隐映射着乐队对于现状的不安,对“黑暗”“围栏”和“迷雾”的反抗与焦迫。
如同主唱王宇所述,同时期出道的很多乐队,在今天要不已经成为“前辈”级别,要不就已经解散偃旗息鼓。而在这片音乐场景之中,当下的埃莉诺偶尔会感到力不从心。
在王宇眼里,他把创作的过程比喻为将自己身体逐渐撕碎的过程,需承担着一种极大的内耗,而且总会面临灵感与精力的干涸与枯竭。“ 要是在那一刻到来之前,眼前的状态始终是门可罗雀,那做这一切的意义在哪里?”王宇也会这样诘问自己。
对一名创作者来说,意义感需要受众的正面回馈来支撑,而表达的失空的确令人沮丧。
“但如果我们放弃了,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与王宇时常审视和怀疑自己不同,鼓手胡畔从不自我怀疑。从小到大,胡畔都是长辈与朋友眼中的“全优生”,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英国,后来回国在不同的音乐媒体供职编辑。经验与自信告诉她埃莉诺的歌曲“无论从作品质量、好听程度和现场表现来讲,不比任何一支乐队差”。作为事业和生活中的双重伴侣,胡畔的这份肯定,给了王宇信心和支持。
2020年5月,乐队发布新歌《放你进我的行李箱》,这首立意“悬疑”“凶杀”的作品,起初却是王宇在旅途中因为思念胡畔而写给她的歌。
作为一支仍在创作的“中生代”乐队,时间、精力和创作的空间是珍贵的。在一则采访中胡畔袒露自己的思虑,“我们只是担心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再好的东西也会被淹没。” 而这也是不止于埃莉诺在面临的困境。
我追问:“如果时代对于内容的期待和筛选真的是这样的趋势,你们怎么办?”
胡畔给了我一个埃莉诺的答案,末了,她又答了句:“如果实在行不通,那我们就选择退出行业。”
王宇跟了句,“附议。”

王宇和胡畔,以及家宠“支付宝”
打开埃莉诺是王宇与胡畔的十年
王宇作为埃莉诺的创建者,最初喜欢The Stone Roses、Kasabian、Black Rebel Motorcycle Club、The Black Keys 等乐队,不可避免这些偏好在后来都成为埃莉诺基因的一部分,想先请王宇回顾一下自己接触摇滚乐的启蒙经历,以及最初如何从“聆听者”转变为“演奏者&创作者”。
王宇:
和很多人一样,我初中开始弹吉他,不过那时候我最喜欢的音乐类型是嘻哈和古典乐,梦想是当一个rapper。当时还流行打口磁带和CD,我记得身边朋友都在花高价四处找Nirvana的《Nevermind》,可我五块钱就能买到Eminem的《The Slim Shady LP》——还是无伤的,开心得要死。

《The Slim Shady LP》,Eminem
1999,Interscope Record
不过不久后,嘻哈迅速进入了主流市场,特别是中文流行音乐里越来越多地出现“有事儿没事儿说两句”,这让我觉得说唱变得有些没劲。而彼时摇滚乐进入了Nu-Metal的时代,Korn、Limp Bizikit这些乐队才是酷小孩的最爱——而我自己也开始被失真吉他深深吸引。
转变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发生,但是身体里的一些东西还是没有得到完全地满足。高二的时候听到了Oasis和Blur——当磁带放进Walkman,《Tender》的第一声吉他响起,我知道我可能找到了自己一辈子都想干的一件事儿。
胡畔应该是在埃莉诺发行《马戏团国王》之前加入了乐队,了解并加入埃莉诺的契机是什么?对这支乐团的初印象是怎样的?
胡畔:
我在2012年加入了埃莉诺。当时我在做一个关于乐队不插电的录音项目,结识了埃莉诺乐队。对埃莉诺的初印象是感觉主唱脾气很不好,很难接近的样子。
之后因为工作关系,我和王宇聊过一些关于音乐的话题,逐渐熟悉起来。当时的鼓手因为一些个人原因不太能继续专注在乐队上,而我那时候正在学打鼓,已经学了一年,虽然还很菜,但王宇觉得我乐感比较好,在他的邀请下我就加入了乐队。

胡畔在曼彻斯特老特拉福德球场
可能会聊到一个比较俗套的问题,王宇和胡畔在后来不仅是音乐事业的伙伴,更成为生活中的伴侣,两位是否可以讲讲对方身上最吸引自己的某个特质是什么?以及在共同的音乐事业中,两个人各自承担着怎样的角色与职能?
胡畔:
跟王宇交往可以说充分感受到了霸道总裁的碾压,就是很霸道。“我说啥是啥,你说啥,那不行”那种。很多时候我都会很生气,不过通常他都比较在理……总之他就是很讲道理,却不会哄人的那种蠢直男。
此外,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,正义感很强。属于世界末日时要出来主持人类公道的那种人。他很为人类的未来担忧,所以我时常感觉自己很渺小……
在工作中我主要是负责鼓的编曲,然后给他写的旋律提出一些意见。我们也会拿demo出来在排练室完善;其它时候,我会负责一部分宣传,写稿子之类的,毕竟是老本行。
王宇:
胡畔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,非常富有同情心,并且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极其天真。作为一个双鱼座,她其实很愿意迁就别人,这正好跟我比较互补——因为特别是做事上,我是比较“我要我喜欢”的那种人。
创作上目前主要还是以我为主,因为怎么说——我们俩无论在旋律,还是歌词方面的逻辑实际上可能是反着的。比如我们第一张专辑《马戏团的国王》里面有首歌《Teenager》词就是胡畔写的,到现在我都没背利索,经常唱错。现在基本就是我写好歌,大家一起讨论,特别是歌词,胡畔会参与进来修改。
两位都曾供职于媒体杂志,看到的资料是王宇在一家时尚杂志,胡畔之前在《Q》,可以讲讲目前两位在从事什么职业;以及工作、生活与音乐事业之间的时间配比是怎样的吗?
胡畔:
我做了十年音乐媒体,在《Q》杂志做了几年编辑部主任。后来不想做媒体是因为不想报道比自己差的乐队哈哈哈……
现在我主要在做二手奢侈品的买卖,自学了奢侈品鉴定。虽然每天大额进出金钱,不过留到自己手里的其实不多,说白了就是赚一个帮别人选货、鉴定、保养的服务佣金。
至于三者的时间协调,其实很难调配,我每天都觉得时间不够用。
王宇:
我本科学的是机械工程,但研究生考了文学院,主修新闻传媒。我当时的计划是毕业可以进入媒体,一来可以借由媒体传播自己的世界观,其次媒体不用坐班儿,我就会有足够的时间用来做音乐,事实上这十年我差不多也就是这样过来的。
大概三年前,我辞去了最后一家杂志的职务。因为从早些时候开始,除了乐队,我也开始做一些配乐、制作的工作。双线进行到一定程度我发现无法兼顾,想继续提升自己,做出更好的作品,就必须专注才行了;所以目前我的时间基本全部都用在听音乐、练琴、学习和工作这些事情上。
说到都曾在媒体工作,两位在日常生活中,除了“听歌、写歌和表演”之外,还有哪些共同的爱好呢?在音乐之外,各自有哪些兴趣的着落?
胡畔:
王宇是曼联球迷,所以我跟着他看了三、四年足球。今年因为看了《Drive to Survive》的F1纪录片,变成F1车迷了,我最喜欢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。
是不是你以为我俩共同的爱好是看看话剧,看看展览之类的——nonono,我俩是double蠢直男,哈哈哈,不过我们会一起看很多电影。
除了做生意和练鼓,我还在练习芭蕾,主要是为了调整体态,有一些美感。

胡畔
王宇:
胡畔说得都差不多了,我们俩也都算老二次元了,动漫方面也有很多说得来的东西。我是机甲类作品爱好者,是要效忠吉翁驾驶扎古的男人,但在胡畔眼里机器人都是一些“小怪人儿”,她把所有的机甲都叫小怪人儿,令人生气。
此外我小时候接触网球比较早,大学时打得很多,后面一直断断续续的。去年开始我重新请教练每周训练,希望能早点达到自己满意的水平,可以多去打打业余比赛。

王宇喷涂的ZakuII,沙漠涂装
今年埃莉诺成立也已经12年了,在中国其实是蛮有意义的一个节点。回顾过去12年乐队历史,请举出几个具有关键意义,或者让自己印象深刻的事件和经历吧。
王宇:
我想说埃莉诺的第一场演出,但发现死活也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在哪了。
2012年,当时胡畔刚刚加入,阵容趋于稳定,我从已有的作品里挑出四首,做了一张EP《The Missing Queen》,由同样独立运作的——我们的朋友朱焰烽的友谊唱片发行。
拖特巴士乐队的吉他手小猫和乐队合作过一段时间,也是通过他我认识了我们的制作人吴涛,并且一直合作到现在。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通电话,面对达达乐队的吉他手,我都丝毫没有紧张,哈哈。将近十年下来,涛哥一直在帮助和鼓励我们乐队,而我作为一个后辈制作人,在业务上也学到了很多。
2015年乐队发了第一张专辑《马戏团的国王》,接着克服了很多很多的困难,我们自己组织了第一次的巡演,去了16座城市,包括澳门。

埃莉诺2015巡演澳门现场
在澳门我们住的酒店应该叫维多利亚大酒店,我记得当时chek-in之后我去洗澡,洗完发现一直戴着的手串不见了。你知道香港、澳门的酒店就那点大小,可怎么也找不到。后来演出完,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宵夜,知道我们住处后笑着说:“你们看过《人肉叉烧包》内电影么?这是个真实案件改编的,当时那家店就在你们住的酒店那个位置……”可能手串给我挡灾了。
12年,两张EP,两张全长唱片,N支单曲和每年一首的圣诞单曲。我们演过音乐节的主舞台,也去过地产楼盘的业主周年庆祝活动。巡演也经历过观众最少时不到10个人,可里面却有五六个都是从外地赶来特意看我们的。
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瞬间都像是刚刚发生过一样。
埃莉诺乐队,现在进行时
在“光芒万丈2020”阶段的巡演中,整体售票情况怎么样,是否达到了自己的预期?我在一篇采访中看到胡畔说过似乎有几站观众不多,这种落差感是否会造成对自己作品水准或者自己音乐形式的怀疑?
王宇:
讲真,处于这么一个状况,特别是我们,可能是自己这圈人里唯一没红没上电视的吧,然后看看自己的数据,你是一定会自我怀疑的。会有一段时间,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错的。作为主创,实际上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一种无形的恐慌中,因为任何形式的创作都是一种极大的内耗,可以说是把自己的身体用力撕破,然后又摆出最好的姿态给别人看——但人迟早要耗尽,身体迟早会撕碎成渣,要是在那一刻到来之前,眼前的状态都是门可罗雀,那做这一切的意义在哪里?
但怀疑之后就要尽快打消这些念头,我曾经比较幸运地和The Stone Roses的贝斯手Mani聊了一小时,当时我问他你能给我做乐队一些什么建议,他想了想说“Focus”,我觉得自己受用至今。

Mani,The Stone Roses
胡畔:
我从不怀疑自己,因为我们这支乐队无论从作品质量、好听程度和现场表演来讲,绝对不比任何一支乐队差,至于落差,当然是有的——落差感只会让我们更加努力精进业务,因为我们不想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成为up主、蹭热点、拍小视频娱乐观众等事情上。
时间已经很不够了,我们都要专注练习,做出更多好作品——总会有好起来的一天。

《光芒万丈》,埃莉诺 Elenore
2019/11/20,麦田音乐
对于当下的埃莉诺,如果以客体视角去旁观他,你们觉得自己在国内的摇滚乐&独立音乐场景之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或位置?同时,通过对自己的作品,尤其是最近专辑和单曲作品的审视,你们希望未来埃莉诺在这个音乐场景中达到怎样的位置和坐标?
王宇:
数据上看,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——没有年轻乐队的年龄优势,而同龄人要么已经偃旗息鼓,要么就已经成为“前辈”,而我们正在一个流量的洼地里陷着。
如果从作品审视,我觉得目前的处境很不公平,埃莉诺应该至少演千人级别的场地。不过说这么多,如果我们失望放弃了,就什么也没有了。
很长时间乐队的一切事务似乎都是自己包揽DIY,就宣发来说,从平面媒体出身的你们在互联网和新媒体不断嬗变的今天,是否会对埃莉诺的企划和宣发感到力不从心,或者迷茫?
王宇:
在签约麦田音乐后,事情好了很多,我们可能更专注在音乐上。
2015、16年我们自己做的两次巡演,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写新闻稿,整理照片,群发给自己认识的所有媒体,然后再背着沉重的设备赶路——为了还原最好的声音,我常常会带两把吉他巡演,等调完音上台都已经累得不想演了。
至于对新媒体的适应,虽然我们是平面媒体出身,但我们上网早啊。我和胡畔基本都是国内第一批拨号上网的网民,blog时代胡畔的ID其实还蛮红的,而我又热衷各类科技和互联网产品,所以其实我们都挺明白自媒体时代。
但我不喜欢音乐人UP主化,随着年龄越来越大,也越发不喜欢参与热点的讨论,像胡畔说的,有限的时间我想把音乐做得更好,至少一点一点突破我给自己定的标准。这个行业有它的特殊性,也许人设红一时,但长久来看,我认为还是要有立得住的作品。
至于算法这个东西,我还不知道怎么打破它。就像你上淘宝搜几个衣架,它就会循环给你推各种衣架。音乐app也是这样,流行City Pop的时候,你听了几首很喜欢,接着可能日推就都是这种,排斥掉其它的可能性,我看过数据,我们的歌不是大家听了不喜欢,而是根本就还没多少人听到过。
胡畔说,“我们只是担心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再好的东西也会被淹没。”如果时代对于内容的期待和筛选真的是这样的趋势,你们怎么办?
胡畔:
我们不能怎么办,我们只能坚持做自己相信的那些事和自己有要求的品质,否则过去的坚持都没有意义了。如果实在行不通,无法阻止娱乐化,那我们就选择退出行业。
王宇:
附议。

王宇和胡畔
如今对埃莉诺的音乐、人设和风格定位是怎样的?加入麦田音乐后,厂牌对乐队的发展的思考和规划带来了哪些新意?
王宇:
我觉得可能随着我们越来越哥哥、姐姐化,人设兴许更容易点儿了吧。大概属于“耕耘多年,现场很稳,但还没被发现的宝藏乐队 ”?哈哈哈。
胡畔:
狼哥对我们非常支持,合作《巴塞罗那的摩天轮》这首歌是和团队的努力分不开的。我们常和麦田音乐的工作人员一起开会,他们都是一群很爱音乐的小朋友。有时候看他们皱着眉头给我们想点子,做策划,也觉得很感动。你会感受到还是有很多人在意好音乐的。
对于即将开始的新的巡演,无论是在编制、编排、曲目以及服化道和视觉上,有哪些针对性的设计吗?
王宇:
和去年一样,我们是四人编制,曲目有所变化,加入了新歌。这次我们在声音呈现上做了更多功课,对现场表演充满自信。
胡畔:
可能从服饰的角度上,我会更注重发型一些,毕竟鼓手一般就露个头。之前总喜欢穿黑色T恤,可能在舞台上会显得有点单调,现在乐队的音乐更加复古化,到时候我们的装扮也会更加复古一些。

埃莉诺乐队2021“光芒万丈”巡演正在进行
点击原文跳转购票
最近关于乐队在现场使用program引起争议的情况,同样会在表演中铺program的埃莉诺怎么看待?
王宇:
我们乐队从创建伊始就会在现场用program。
我也知道最近有关于这事儿的讨论。我看了那些视频,并且后面话题突然就变成了现场能不能用program——觉得很气愤,我认为这完全是跑偏了,并且误导了行业外的乐迷。
在编曲里使用大量的合成器,管弦乐甚至打击乐,这是非常常见的。然而以大多数乐队的实际状况,你总不能带着几十斤、上百斤重的设备和一个乐团出去巡演。我可能有一首歌的主题是用单簧管演奏的,但就为这一首歌——没办法多带个乐手。所以出现了同步播放program这个办法。
简而言之,它是在现有的条件上让现场音乐更丰满,更还原创作者意图的办法,而绝对不是帮台上乐手偷懒的工具。
对于这场新的巡演,有哪些期待?
王宇:
我是天津人,这是我开始创作音乐差不多十七八年以来,第一次在天津做专场演出。
胡畔:
有好几个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,希望吃到一些好吃的。

王宇在大阪环球影城EVA限定
新歌、回顾与创作谈
在《光芒万丈》之后,乐队陆续发行了许多新的单曲,在包括专辑在内的新歌中,你们各自最喜欢哪一首?
王宇:
《清醒之伤》,摇滚乐嘛,演着更来劲,巡演每一场我都盼着赶紧到它。(胡畔:你就是想累死我。)
胡畔:
《放你进我的行李箱》《清醒之伤》和《巴塞罗那的摩天轮》这三首歌,是我们越来越好的一个证明。这几首歌都非常好听,我真的很难选择出最喜欢哪首,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都听一听。
在两张正式的专辑和一张EP,以及一些零散的作品组成的埃莉诺12年乐队历史中,王宇觉得乐队在创作上是否经历过明显的转折或者转变;此外,现在回顾整个创作的时间线——以作品出版时间为节点,以作品的成熟度或者在内心的满意度为评判的标准,你们的创作是否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?
王宇:
2012《迷失的女皇》和2015《马戏团的国王》和所有乐队的首张EP、专辑一样,我们把之前积累的所有关于音乐的想法都放了进去,充满原始的冲劲儿,虽然现在看不是特别成熟。
《Into The Shadow》2016就出了,我想把东西做得更简单、直接,去掉了大部分的合成器元素,以三大件+原声弦乐组和打击组完成表达——这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。
《光芒万丈》实际上2018就做好了,音乐更多元化,也更成熟,当然我看到一些意见说有点流行,我自己是没感觉出来,它是一个进化的标志。
加上新的这些单曲,我在准备第三张专辑。我觉得我们的创作风格从来没有发生变化。我一直认为一个真诚的创作者就是——你是什么样的人,自然就做出什么样的音乐,你可以连着听我们所有的作品,固执的内核从来没有变过。
就上面的问题,想请胡畔补充自己的看法和意见。
胡畔:
我们两个时常讨论这些问题,所以他说的基本上涵盖了我的意见。有时候我可能会更趋近于比较流行化的旋律走向,但是王宇有自己对于艺术的坚持。那么fine,不可能每首歌都是金曲向的,所以大部分时间我没有什么创作方向上的意见。
由于第一张专辑《马戏团的国王》和后面的歌版权不在一个平台上,所以有很多新歌迷可能对老歌不熟悉,这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。希望大家也能听听第一张专辑的老歌,有点糙,但是特别带劲。

胡畔 摄影/小贝
在EP《Into The Shadows》中,你们创作的灵感来源于游戏,而如今的新歌在创作灵感上似乎更多来源于生活中的具体经历,是这样吗?可以谈谈在创作的灵感这件事上,今天埃莉诺的创作的灵感更多是来自于哪里吗?
王宇:
只有《Bad Blood》那一首歌是来自游戏《血源诅咒》。看过的书,电影,心里一瞬间的哀伤,都是灵感。
2019年因为人员变更,我作为现场吉他手和盘尼西林演了一年,正是乐夏热播,演出很多,几乎每周都有出差。起于对胡姐的思念和歉意,在一次往返的航班上我写完了《放你进我的行李箱》,后来她看完歌词觉得有点平淡,最终改成了现在这个关于凶杀的故事。
胡畔:
这首歌被周迅推荐了,我感觉她可能是喜欢歌里那种电影感吧。
就乐队、作品、巡演,王宇和胡畔还有哪些想告诉乐迷或者分享给大家的吗?
王宇:
请大家来看演出,不会让你们失望。
胡畔:
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听到我们的歌,可以来到现场看一场高水准的表演。能在现场看到歌迷和我们一起唱歌才是最开心的,其他的都不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