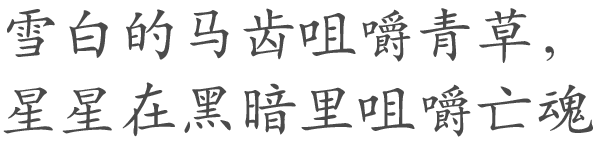中国摇滚,猝不及防的遭遇



编者按
一档大众综艺节目《乐队的夏天》彻底颠覆了中国独立音乐的全部语境。滋生于物质与精神双重贫瘠的年代,从10元三张的塑料垃圾里吸取全部营养的地下音乐人,在“乐夏”的舞台上给几乎没见过磁带或者CD的90后、00后看到的,是他们几十年用无望和挣扎堆积起来的财富。然而,在乐评人孙孟晋眼里,这时代猝不及防的真相,是你经常一不小心,就被锁进一种不自由的套子里。
做一样事,认真坚持十年、二十年,除非特别没有才华,总会熬出头的,现在中国大多数独立音乐人都是这样。然而,世界万物总有它的衰败期,情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。
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,在资本决定了大半个地球的时代,人的脆弱与薄情,又往往把某些古老的尊严弃之敝屣。谁都想在这个随时都有可能被遗弃的时代留有一席之地,有的一夜爆红,有的一落千丈,这都是天意。但大家太认同一种俗世的成功,自设人设,降低行业标准,当然也是必然的事情。
中国几代摇滚人,恐怕都低估了人性的复杂,低估了每个时代都要付出的代价。
现在给“老音乐人”埋单的,大都是年轻的一代,90后,甚至00后。这种隔层的关系,来得太突然,也来得格外令人欣喜。这是一代美好的一代,他们不需要启蒙,他们自己启蒙自己。现在听摇滚现场的,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,当年那些忠实的粉丝都在为生存打拼,他们只有怀旧的自觉。

人,总是缺什么补什么的。摇滚与独立音乐,对于最早的那代中国乐手来说,认识到和西方乐手的差距,他们大多很轴地炫耀的也就是技术这些东西。浸染“打口文化”(指在信息闭塞时期,外国唱片以废塑料大量进入而影响音乐的普及和审美)营养的新一代,他们不仅拓宽了表达,也纷纷消化了吸取的对象。他们中最出色的这批基本都不出生在生活优越的家庭,贫瘠的世界给予他们早熟和敏感。这种财富是由无望和挣扎堆积起来的,并且很快加入反抗的阵列。所谓反抗,最后发现反抗的是自己设置的陷阱,因为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需要足够多的世故和套路。
很难说,摇滚在当年是态度多,还是青春的荷尔蒙多,2000年前后,是这批当下仍然很活跃的音乐人的成长期,我曾经在树村、霍营的北京地下音乐村住过,后来生活富裕点了,很多人到大理去了。那时,我分别住过高虎和朱小龙家,高虎处在“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有反抗”时期,他租的房子很小,一切都像处在孕育期,他和痛苦的信仰乐队的胚胎是说唱金属,墙上贴满的倒是披头士和猫王的海报。我说,你要知道约翰·列农(John Lennon)在比你小的时候,床边贴的是猫王和毕姬·巴铎(Brigitte Bardot)的海报。

那晚,我说了一堆摇滚轶事。生活是玩笑,要到很后来才知道,这些最多是青春的摆设与误区,不如夹杂着苦涩和幸福的微风来得更直接,高虎的墙上没有贴美女的照片,我明白他还是成长期的男孩,有一天他会上别的船,并义无反顾与那个岸道别。朱小龙是很直的男人,当年舌头乐队里的硬朗有一部分和他有关,他是一个能让爱情在高原存放的男人,他的内心世界里有一种厌恶虚伪的天性,并要随时划清界限。他是当时地下音乐圈最让我感受温暖的人。
人性里有灰色地带,人生,就是穿过灰色走向不同的岔路口。包括老了,成为年轻时反抗的那个人。舌头乐队是这一时期顶天立地的乐队,但他们保持贲张的现场的周期并不是很长,随后就是时代无情的翻篇。“舌头”的灵魂吴吞以前随身带个小簿子,记录他的灵感,他血液里是摇滚分子,有一天,也孤独得弯下了腰在民谣的天地里徘徊,他会暴露那种修正,因为他注定是一个“杀手”。他也是这代摇滚人中最好的诗人之一。“舌头”以前的专辑都被海外混音师混错了,他们像一块被颠覆了出生的化石。今年,新“舌头”的唱片《怎么能够说我爱你》是吴吞当下状态的真实反映,偏暗黑民谣风格,讨论了这个世界的欲望和逐渐老去的孤独。这种对比是真诚的。

舌头乐队从顶天立地的摇滚乐队,
逐渐转向暗黑民谣风格
我不反对娱乐节目,尽管它有先天的套路。它肯定不是唯一的,但这也是当下中国独立音乐在大众和小众之间的桥梁。“乐夏”难免收拢了一大帮早就成功甚至老去的乐队,在欧美有偶像唱歌大赛,但绝对没有把“北极猴”(Arctic Monkeys)和“电台司令”(Radiohead)统统请去的比赛。因为,他们的音乐多元性的生存土壤足以让他们收获商业的价值。
我很欣赏“五条人”在“乐夏”的表现,他们的“出圈”,并不是来自讨好,恰恰是一种恶搞的态度。仁科真的像大张伟吗?“五条人”掌握了迪伦式的恶搞技巧,对于媒体和公众,鲍勃·迪伦一直闪烁其词,他不会在浅薄与曲解的死胡同里寻找生路。或者,那句名言更准确:“幽默是无聊透顶后的优雅表现”。
“五条人”出道相对要晚,他们早期的几张专辑《县城记》、《一些风景》和《广东姑娘》达到的成就,也只有一个被渐渐遗忘的名字——胡吗个的专辑能殊途同归。“五条人”的南方市井气里的忧伤,一旦混杂了滑稽与朴素的对立,那种神经质的出格就是底层世界里的“挑衅”。他们的歌词也出众,尤其海陆丰地区的语言魅力,在华语音乐里,唯有林生祥才能制造这种韵味。现在的“五条人”现场越来越有随性的无厘头,这点和“顶楼的马戏团”不谋而合。

失败有伤害,成功也有伤害。“受困”的人群在某个角落呆久了,一旦气球升空,还是需要悄悄降落的。其实,“五条人”并不怪诞,如果你真的进入他们的生活,就知道这是他们的常态。他们把生活的荒诞尽情地调侃了。
这个时代的残酷,是经常一不小心就被锁进一种不自由的套子里。迪伦真正的厉害不是他早年的反叛文化代言人角色,而是他始终保持一种警惕。他也从来不会对着资本大献殷勤,那种傲骨是天生的。我经常看到有些年轻小乐队面对摩登天空老板沈黎晖,像见到了爹一样,亲爱的小朋友,只有你有价值了,你才会被尊重。
茂涛他们曾经是卖打口唱片的,左小祖咒也是。这几代音乐人很好地自我进行了音乐审美的补课,今天看到各种知名人士一个个开始讲爵士,这都是一堂自我“进化”课,不管是不是装的。我和左小祖咒早在1992年就认识了,我给他取了一个不太吉利的艺名——诅咒,大概他发现诸事不顺,后来,把“诅”字改成了“祖”字。他现在经常会说:一身“鸡贼”的本性随时发光。他有插科打诨的能力,他的渴望成功是一部人间山海经,他和自己较劲也是难寻其右的,这一切源于他过早地洞察世界。人类历史,很多时候是一部虚妄的历史。他早期的几张专辑是中国摇滚史的重要篇章,他也是这代人里面恶搞的祖师爷,最后真假难辨。他也是最早把唱片卖到天价的人,他毫不忌讳收割的勤快。

左小祖咒有插科打诨的能力,
他的渴望成功是一部人间山海经。
摄影:陈旭人人
左小是我平时听得最多的摇滚音乐人,经常听的是《大事》、《美国》和《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》这几张,这里面有生的裂痕和悲哀,他的复杂性是我喜欢的地方,轻而易举就把各种人间真理和歪理组成很有质感的诗句。这是一部沧桑史。左小居然出了近40张录音室专辑,大家都跟不上这种节奏了,也跟不上他“表演性”的变调了。
人,会各自走到面目全非?不管是黑的,还是白的,最初的情谊总是红的。
毫无疑问,这批人中有很多天生的音乐人,如小河,如马木尔,还有宋雨喆。小河自从信佛了,像变了一个人,他经常把倾听当作一种布道,我非常喜欢他的率性,和与时间一起流逝的自由。“寻谣计划”其实是有个前提的,民间存活的东西一旦消亡,还有找回的意义吗?他可能更想唤起我们孩提时的纯真。但一次次在干枯的河道里,围在老人边上起舞,不是一种新的惯性,新的套子吗?小河的才华远高于重复做这些事。

小河的“寻谣计划”
对于周云蓬对世事的体察,我一直很敬佩,从而对他进入古诗词的天地无法适应。他是中国少有的具有伍迪·格瑟瑞尔(Woody Guthrie)气质的人,他是一个诗人,他的诗歌领域里有体味平常百姓的敏感,这种叙事体也是一种出色的寓言体。
万晓利,有一阵觉得他被裹挟得很远,近日在他的《北方的北方》纪念音乐会上,感受到了挡在他和我们之间厚厚的高墙的孤独,那是一道亮光,走在西伯利亚的雪地里。
张玮玮的爱好很文艺,有皮亚佐拉的境界,他的音乐性好到可以和各种领域的音乐人合作。所以,和质朴的“野孩子”不在一个维度里。我对拉手风琴的人会有一种天然的停留,偷偷识别一下,他是黑夜的街角的,还是安哲罗普罗斯的神话风景里的。

顶楼的马戏团是我内心一直最靠近的上海乐队,他们的音乐不就是我们的写照吗?在这样一个其实很难感受到野性而过于精致的城市里,几分扭曲,几分迁就,陆晨和梅二身上的小市民气质和摇滚精神一直格格不入,我说小市民一点也没有贬义,它是我们生活的大部分,既然你不选择虚伪,那就把自嘲与荒谬加倍混淆。
我本想提及更多的音乐人,尤其前卫领域的。这些年,接触了各种艺术领域,我知道它们本质上是相通的,当你在善意的世界里前行,愈发体察你自身的变化。人生,就是不断地在走向目标时,主动和被动地停下来。
乐队,和人的关系一样,分分合合,毫无必要永恒,或者大合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