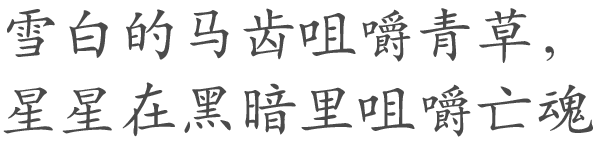周云蓬:一个盲人和他的民谣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特约撰稿 刘芳
“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,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;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,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……”
六月三日下午,圆明园单向街书店的小院里传出悠扬而深沉的歌声。小院中聚满了人,核桃树叶子在微风与阳光中沙沙作响。
歌者戴着墨镜,长发及肩。在倾听现场听众提问时,他不是将目光投向你,而是把耳朵转过来找你。他是一个盲人。
他叫周云蓬。新民谣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受单向街书店邀请讲唱中国民谣。文章开头的歌就是他不久前推出的专辑《中国孩子》里的主打曲目。
相比他2003年发行的注重诗意的首张专辑《沉默如谜的呼吸》,在《中国孩子》里,周云蓬对社会现实投入了更多的关注——从专辑里的歌名就可以看出这一转变:《买房子》、《黄金粥》、《一个儿童的共产主义梦想》……
旅行
“看不见了,就等于关掉了一条路,音乐就是我自己修的通向世界的路,”周云蓬说,“别人沿这条路给我送水送吃的来,我给他们送别的东西出去。”
1970年,周云蓬出生于辽宁。在一篇文章中,他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:“9岁时,彻底失明。留在视觉中的最后印象是动物园里的大象用鼻子吹口琴。这大概是后来我弹琴写歌的最初动因。”
17岁,周云蓬瞒着父母一个人跑到了北京。“印象中那是个特别热的夏天,走两步就得买个冰棍儿。”这是他第一次独自出门旅行。这段经历给了他充足的信心,他发现“什么路都能走得到,不行就向人打听。”
1995年,周云蓬大学毕业,分配到一家色拉油厂工作,忍受了几个月他称之为“苟活”的日子后,辞掉工作,又一次来到北京,卖唱为生。
他住在圆明园——当时那里是流浪北京的文艺青年聚集的地方,只要天气不差,他一大早就出来在北大门外卖唱,常常一唱就是一天,“那时候卖唱比较新鲜,好的时候一天能有一百多块钱。”
晚上回家,走在荒芜的圆明园里,稍有风吹草动心里就发毛,“因为看不见,所有的感觉都放大了。”
1995年年底,周云蓬去青岛大学演出,随后又去了上海、杭州。从此,他基本每隔一年都要远行一次,湖南、云南、西藏、宁夏、甘肃……每到一处,他都在当地住上一段时间,找个酒吧或茶馆演出维持生存,慢慢了解那里的生活。
“每次旅行对我而言就像是洗了次温泉浴,全身都通透舒服,心胸也变得开阔。”周云蓬笑着说,每次离开久了再回来,就觉得北京很多地方都还是不错的,很多人也是很可爱的。而且,旅行让他不会执着于什么人或什么地方,“不会觉得离开谁就活不下去了。”
2000年底,周云蓬只身踏上前往西藏的道路。在登上唐古拉山的那一刻,他留下豪言:“我是世界壮丽的伤口,伤口是我身上奔腾的河流。”
半路上他出现高原反应,在那曲下了车。在那曲的那几天他认识了藏族姑娘卓玛,卓玛给周云蓬找了家酒吧,他成了那里惟一的汉族歌手。“我在上面唱,底下一呼百应,他们最爱听林志炫的《单身情歌》和刘德华的《爱你一万年》。”
归途中,周云蓬把卓玛的电话号码弄丢了,和她失去了联系。卓玛永远留在了他写的《今夜》的诗句中:“我想起卓玛,那曲的草原宾馆,有牛粪的香气……”
在拉萨,他发现不少藏人消费特厉害,“要啤酒都是一箱一箱的,有的还特洋气,爱听英文歌,你唱汉族歌人家还不爱听。他们还知道《加州旅馆》呢。”
2005年,周云蓬与妻子又去了次西藏,这次走的是滇藏线。他专门买了一个MD,收集听到的各种新鲜的声音。晚上在路边宿营,他听到许多种鸟叫,“跟北京的鸟口音完全不同,太好听了,北京连鸟叫都是普通话。”
“西藏让人上瘾,去了还想去。”他今年还打算再去一次西藏,走川藏线进去。“旅行像吃饭、买房一样重要。而且很实在,能化成一种物质存在你身体里。”他说。
“人应该多一些情趣,有情趣你在北京街头也能发现各种有趣的事情,没情趣就是把你放在珠峰,你也会觉得这有啥啊,不就是一片白吗?那就没劲了。”
大多数情况下,他都能坦然面对黑暗中的生活,但总有些时刻令他不能释怀。比如旅途中看不到风景的时候。其它东西可以靠想像,但“你又不能摸出雪山有多高。”
家生活
周云蓬的家最近刚从香山搬到了宋庄。
他们的家有两间大屋子带一个宽敞的农家院,院子里种着香椿树、玉米和黄瓜,还拴着一条小白狗——是他们在路上捡来的。
因为家离市区远,周云蓬搬家后很少在晚上去酒吧演出。他通常早上五点多起床,念文殊菩萨的心咒,这是他结识的一位西藏上师传授他的,“文殊菩萨是管艺术的,念经对心智有好处。”周云蓬说。
他还开始尝试吃素,嗜好喝酒的他,也逐渐开始控制,“宗教让人宽容,过去容易患得患失。”
新家不能装宽带,周云蓬便把自己早先创立的民谣网站“马齿民谣”交给别人管理,
“而且网站技术我也不是太懂,做起来费劲。干脆把它做成个怀旧网站。”
他家的电脑没有显示器。键盘、音箱摆在书桌上,主机藏在下面。他在电脑上装了一个语音软件,可以把页面上的字读出来。他下载了不少电子书,有空就让软件读。
周云蓬最近在听费尔巴哈的《宗教的本质》,当代小说家里他最喜欢莫言,说莫言的《檀香刑》写得很押韵,好听。
除了“听书”,“听电影”也曾是周云蓬最大的乐趣之一。在第一张专辑里,他有一首自传性质的歌曲《盲人影院》:“有一个孩子,九岁时失明/常年生活在盲人影院/从早到晚听着那些电影……”
周云蓬以前爱“看”央视六套的“佳片有约”,大多是译制片。他很喜欢伯格曼的《秋天奏鸣曲》和越南影片《恋恋三季》。他得意地说:“能靠听把电影听明白,需要多少想像力啊。”
不过现在他却几乎不听电影了,“没什么国语的电影,都是外语片。就连国语的也听不了,好不容易有个《疯狂的石头》,还是四川话,听不懂。而且现在的电影台词越来越少,像王家卫那种,半天说不了一句话。电影都拍成这样的,我就完了。”
新民谣
周云蓬把自己与小河、万晓利、野孩子、赵牧阳等人的音乐称为“新民谣”。
在周云蓬看来,新民谣与高晓松等人的校园民谣的最大区别,是新民谣带有强烈的草根性与社会现实感,因为“我们更多是在城市鱼龙混杂、泥沙俱下的环境中挣扎的人。”
对校园民谣,周云蓬认为最大的问题是“所有的人都是不变的三拍子,好像校园民谣就是青春气息这点东西。其实它没有反映出真正的校园。”
以前周云蓬他们只在酒吧演出,现在他们已经陆续在各地的大学、体育馆开过专场演出和民谣节之类的活动,今年他们还登上了北京迷笛音乐节的舞台。5月30号,周云蓬和小河、赵牧阳、吴虹飞等人刚刚在北大搞了一次新民谣的演出。“说不定不久以后就能上春晚了。”他开玩笑地说。
在单向街演出时有一个听众问他:“你现在是不是从地下走到地上来了?”
“地表吧,说地上好像还没有,说地下也不那么合适。”
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?”
“就是一支萝卜长出土来的过程。我就算不搞音乐,也不能老在地下待着啊,得出来看看。其实每个地层都有自己的圈子和生物链,用放大镜看一下都挺生动的。”
他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:“我到处走,写诗唱歌,并非是想证明什么,只是喜欢这种生活,喜欢像水一样奔流激荡。我和命运是朋友……”